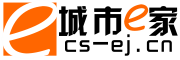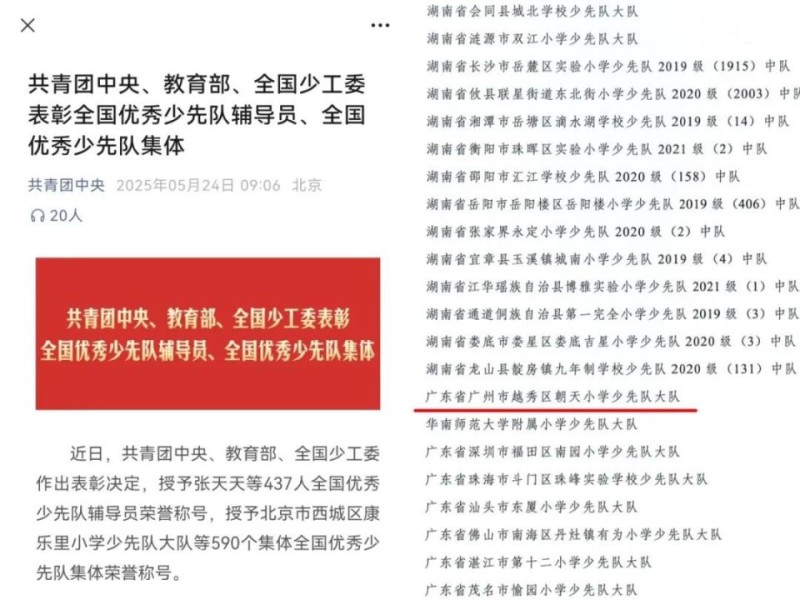《龙中对》由龙岗区委宣传部、龙岗区总工会联合深圳晚报社出品,是一档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宏观背景,立足湾东龙岗,在全球视野、国家立场、双区宏图中展现龙岗担当的原创城市观察类访谈节目。6月7日,《龙中对》推出第六“对”:《交汇的力量》,由《龙中对》发起人周智琛对谈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教授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。郑永年教授是中国问题专家,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长期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,我们整理编发了访谈文字实录,以飨读者。
(访谈前)
周智琛:郑永年教授对我来讲应该是个熟悉的陌生人。早年间我一直在看《联合早报》,而且我也在《联合早报》发表一些文章,就开始非常关注郑永年教授。他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,我觉得他是一个站在地球上看中国的人,而且郑教授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,这所学校就在龙岗,他可以从一个全球化的框架里面对整个龙岗的产业、政策,尤其是在人文社科方面可以做一些建议探讨和研究。
(访谈实录)
关于自己:在知识的王国里
周智琛:听说您喜欢徒步?
郑永年:我徒步。你们可能很少有我这么能徒步的,我有一次一天走了73.9公里(笑),有记录的。跑步我以前也跑,但是后来膝盖坏了,跑步就会有影响。
周智琛:您有跑过全马吗?
郑永年:没有没有,我从来没有比赛、竞争的心态。
周智琛:那这个特别好。
郑永年:我是觉得做学者有个好处是什么东西呢,就假设说你要当一个皇帝,要竞争,勾心斗角,但是你如果要建立一个知识王国,自己跟自己竞争,你不用对任何人。知识的王国就是一个人(笑),真是,多好!对吧?
周智琛:您是天生很会读书吗?
郑永年: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会读书,但是我喜欢读书。当时农村没有书,书很少很少。所以我到了北大以后觉得,哎呀,怎么读书那么容易,那么多书,开心得要死。
周智琛:北大是怎么考上的?
郑永年:我15岁高中就毕业了,当了四年的full-time全日制的农民,然后到1981年才考大学。我(本来)想去考个师范,当一个中学老师。
周智琛:当时就很有面子了。
郑永年:那很有面子了。结果阴差阳错考上北大了(笑)。我考上了以后,我爸爸不高兴,我们家很大,我有四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、一个弟弟,因为当时两个哥哥分家出去了,我要干活了,(我是)劳动力了对吧,我爸说你那么大了怎么爱读书啊。我老爸老妈都是文盲,他们都不知道北大在哪里。
周智琛:反正您,您爸妈怎么样都没想到,您会越走越远。
郑永年:对,越走越远。我还记得我老妈跟我说过,我考上大学了,我老妈去算命,那个算命先生告诉我老妈说,这个人以后会到处走,结果真的成为现实了。我觉得像变成金庸的丐帮似的,到处走,到处去看社会。
周智琛:后来怎么就选择到普林斯顿(大学)读博士?
郑永年:本科毕业了,我们国际政治这些毕业的(学生),外交部、中联部抢着要人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,我还是喜欢读书。
周智琛:后来好像是留校了?
郑永年:就是读书,读硕士。我读硕士三年,那个时候真的,因为为什么强调“天不怕地不怕”?我就主编一套《政治学译丛》,把西方的政治学的这个书翻译到中国来,第一本讲政治学的方法论,我翻译的,你现在去看,现在还在用。
周智琛:好厉害。
郑永年:我们几个人,那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但是那个时候去普林斯顿(大学)也不是计划的,很有意思,因为我也不知道普林斯顿(大学)好不好,有人告诉我普林斯顿(大学)是爱因斯坦待过的地方,那我说这个不错。大家就是要填申请材料,我也想申请哈佛(大学)、普林斯顿(大学)。哈佛(大学)它要求我们,(它)可以把材料寄给你,但是你要交5美元,我就……难倒我了,5美元又没有,怎么寄给美国?那个时候不可能。普林斯顿(大学)很大方,就免费把这套资料寄过来了。结果我GRE(留学研究生入学考试)没考,普林斯顿(大学)就是说,因为我当时翻译了很多的、写了很多的文章,并且他们觉得你写的这个不错,对吧,写的挺好的,普林斯顿(大学)说那不用考了。我觉得很好,就这样去了。
周智琛:您有没有思考过,就是说您的整个知识框架,或者说整个学理的逻辑等等,是在这么几所大学里面建立的,哪个时期会更根本一点?
郑永年:如果这样说的话,其实北大的教育,中国教育的好处,就是基础知识扎实。我到了普林斯顿(大学)以后,到了谈论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以后,我发现美国,我的美国同学反而不懂,他们说不需要知道,这些东西不需要记,就是说这个百科全书,翻一翻就够了。他们不是说你的知识量要多大,而是如何去创造知识。
周智琛:对,创造知识。
郑永年:所以我是觉得,当你学会了如何去创造知识,以前学的知识反而变得有用了。
周智琛:这里面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,当农民的阶段到北大等等,反正就是听命运的安排,但是我后来发现您比如说从普林斯顿(大学)到哈佛大学去做博士后,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,似乎您个人已经非常清晰自己要干嘛了。
郑永年:人的行为,还是有他的purpose,还是有他的目的性。我在哈佛做博士后的时候,受傅高义的影响,就是他做东亚四小龙,所以我决定去看一看。
周智琛:在学术圈,国际方面,给别人印象很深刻,应该还是从新加坡那个时期开始吧。
郑永年:得到关注比较多就是从新加坡我写专栏开始。
周智琛:这点我觉得很感兴趣,这个写专栏应该说,是不是在您的学术生涯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、有分量的一个选择和一个安排?
郑永年: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故意的安排。因为我做政策研究,看《纽约时报》或者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,我看了以后,有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的观点很好,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的观点来看、另外的方式来看,我就试着写了几篇,结果大家反应都不错,所以这个报社也鼓励我写下去,结果一写就写了20多年。当然(联合)早报这块专栏不错,被李光耀先生树为他们国家的名牌了。
周智琛:对,确实是。
郑永年: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读者,美国、欧洲读者都看。
周智琛:那时候已经非常地清晰,反正就是开始研究中国问题。
郑永年:对。
周智琛:中国政策。
郑永年:我的风格就是农民风格,通俗易懂。以前国际关系里面有一句话:“国际关系是最简单的。”我就说是三句话,第一句话就是“外交是内政的延伸”,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,对吧,奥地利军事学家;第二句话就是“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”;还有一句话,以前是美国一个国会议员奥尼尔所说的,“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”,地方政治。把这三句话拼起来,国际关系就全了。
关于开放: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
周智琛: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发现,尤其是国际关系有诸多摩擦。当然中国的大国地位,大国外交我们也都有目共睹。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就是,尤其这十年来,中国也更多地去参与到国际规则的一些制定,也想听一下在参与制定规则方面,您觉得它的重要性,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我们应该更多去关注和去着力的地方。
郑永年:当然就是你提到规则,我是觉得就是全球治理的核心。因为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,这个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,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动荡,也就是全球治理发生危机了。为什么有危机?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些规则无效了,或者不那么相关了,大家不遵守规则了。
再说二战以后,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,但联合国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,联合国就是一套规则,对吧?世界银行就是一套规则,都是由一套规则组成的,大家都认同这个规则,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,这个规则能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行为或者利益,那么我们说这个规则是有效的。就像我们这个班一样的,一个班就有一套规则,如果每一个学生都遵守这个规则的话,我们这个班非常有序,是吧?稳定。
那么现在就是你讲到这个中国的规则问题。所以就是首先要强调中国跟以前的规则的问题。那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现在是第四次崛起,第一次是秦汉,第一次统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然后唐宋,然后明清。唐宋是非常强大,我们就说唐宋的规则,正是唐宋时候的规则塑造了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。
周智琛:对,到现在还是影响非常深刻。
郑永年: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塑造规则的时代。并且中国,尤其要看到,那时候的规则是非常先进的,不是说像现在今天美国一样到处去推行自己的规则。那时候我们周边的国家就是到中国来学习规则,跟中国接轨。
周智琛:完全引领型的。
郑永年:完全引领型的,完全就是我们今天真正所说的soft power,软力量。所以规则首先要有力量。第二这个规则你是先进的,在那个时代是先进的,大家都会来学,你不需要花很多力量去推行的。
但是到现在,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探索,改革开放又再次崛起,那么这个崛起,这个外面的规则,世界规则,已经是以西方尤其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了,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处理跟现在的世界规则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邓小平先生非常伟大,我们先加入世界,我们叫什么,叫接轨。
周智琛:接轨。
郑永年:加入WTO就是接轨。我们为了加入WTO,1990年代系统地修改了我们国内的法律法规、政策体系。
周智琛:应该是全方位的。
郑永年:全方位的,我们开放是全方位的。否则的话,如果没有这样的全方位的接轨,我们看不到今天经济发展的程度。
周智琛:要开放。
郑永年:开放是非常重要的。
周智琛:要接轨首先得开放。
郑永年:对,你要接轨就要开放,开放是本质性的东西。不开放,什么规则,说不上。你不开放,人家也没法来学;你不开放,你自己也没法走出去。那么开放的情况下,规则的背后是什么?就是我们所说的,技术标准、思想的流动,对吧?假如说我们以前是接受规则,我们下一步能不能从一个规则接受者走向一个规则制定者,那也还是取决于开放,开放程度。
周智琛: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开放,可能是一种连接,是一种接轨,说白了其实就是协调利益各方,现在我们要去主动建构。我们有时候也在想,我们如何去跟全球打交道。比如说我们,因为我们做传播,就是我们的国际传播方面,怎么讲好中国故事?
郑永年:媒体的话,现在走出去困难,但我是觉得并不是说媒体走出去困难的问题,而是方式的问题。
周智琛:方式的问题。
郑永年:你讲故事对吧?我给你讲故事就是为了让你喜欢我,对吧?这是我讲故事的purpose,目的。我故事讲了好几年,你更害怕我了,那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肯定不对了。
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时代,中国不是“吴下阿蒙”了。像这几年我们有人在争论,西方也在争论,中国是不是放弃了韬光养晦。那我就说,因为时代变了,不是说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政策,中国以前(上世纪)80年代经济(体量)还小。
周智琛:那时候还挺一穷二白的。
郑永年:(以前)中国的人均GDP 300美元不到,很穷,吃饭都成问题。那么那个时候,你对其他国家,实际上你做什么没有什么影响,你做一点东西人家也不怕你,没有外在影响。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,现在我们(是)第二大经济体,你如果再说以前的韬光养晦的话,那就说不过去了。所以我自己一直说,我们如果是(上世纪)80年代有这个韬光养晦1.0版,我们现在要做2.0版、3.0版,要与时俱进的。你要考虑到周边国家,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到共同富裕。我们以前说“睦邻”,那么(现在)我们还要提“富邻”。你看,所以这些理念都非常好。
周智琛:就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特点,比如说有几户人家,或者我们家很穷,有别人看到我们很穷,他真的对我们特别好,但等家里富有的时候,当你在强大的时候,有些人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。
郑永年: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样的,人心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说,即使同一个国家的人也是(一样)。这就是我们强调要扶贫、要共同富裕,当然我们也尽量去做像一带一路,也是带动我们周边国家的发展,我们叫共同发展。你要考虑到这个周边国家或者邻居或者域外大国,这些,它的利益。
关于未来:大湾区可以建设三大世界级平台
周智琛:这个确实是世界之道,它可能也是力量平衡对抗的一个结果。其实我们想回到我们所坐的这个地方,实际上是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区,我们很想说通过您这种行走全球,包括观看了全球很多的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看我们大湾区,就是实施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方面,您觉得大湾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
郑永年:我早就写过,深圳和大湾区是得天独厚。我到了深圳以后,第一篇写的文章就是提倡建立南方共同市场。什么意思呢,我们统一建立起来以后,我们才能从大到强。我举很多例子,深圳,中国大部分的高科技公司,腾讯、华为都在(深圳),但是我们的互联网IT产业,我们国内有没有统一的规则?国际有没有统一的规则?走出去要不就是美国规则,要不就是欧盟规则。
我一直在提倡我们大湾区两步走,首先就是说我们把香港跟澳门的规则,差距不大,整合起来;第二步,横琴、前海、南沙不用各搞各的了,规则统一起来,以点带面,对吧。香港的那些规则延伸到整个大湾区,我们做“香港+”,Hongkong Plus,香港的规则是国际化,国际都接受的,我们既统一了规则也走向了世界。
周智琛:那么下一步龙岗如何发展自己,带动周边,形成自己的特点?
郑永年:龙岗完全可以(成为)一个东西方交汇的科创中心,科创跟教育联系起来,我们有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……
周智琛:还有北理莫斯科。
郑永年:北理莫斯科。我们现在这两个大学不要再发展中国传统的大学,中国传统那些大学已经很多了,我们要新型的大学,政产学研一体化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解放思想,要先行先试,实践教授只要占一半的话我们就有希望,100%书呆子没有希望。所以我这几天在想如何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知识强国,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做出来。改革开放40年我们多么成功,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我们这个成功的经验转化成为我们的知识体系?这是我们要,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思考的。我们的现代知识体系就是拿来主义,因为社会科学本身就产生在西方,政治学里面第一部最经典的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,到现在为止还在读,都是实证的,把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体都概括一下,把它总结比较一下,把它概念化成为理论,成为经典的著作,这就是连接实践的结果。我们那么多丰富的实践,为什么产生不了理论?这还是我们的思维问题。
周智琛:我来之前也很想跟您探讨,关于人文社科的重要意义。如果从体系的角度来讲,您觉得深圳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安排?
郑永年:有太多东西要做。去年(2020年)深圳40周年,讲深圳故事的很多,除了你们媒体,以媒体的视角来讲,讲一些具体的故事,有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在讲深圳故事?没人。我们现在不用说深圳,北上广深那么多的城市群在崛起,除了经济学家在算这个GDP之外,没有人把它做成社会科学。不能光讲一个具体的故事,一定要跟社会科学,跟深圳的发展结合起来,并且一定要有比较,你要看,放在整个的世界环境里面。深圳的崛起离不开国际环境,这样去看,你怎么崛起的?有什么样的一些要素在影响你崛起?人家衰落了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要素?
周智琛:对,怎么衰落。
郑永年:这个就是慢慢比较出来。因为我们社会科学你不能做实验,不是说像理工科那样,关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,我们要observe,就是要观察不同的点,这个难吗?我觉得不难。
周智琛:对。
郑永年:要有人有意识,我们没有这个意识。
周智琛:郑教授我觉得是这样,我觉得您如果写写深圳,就是从您的这个世界级学者的角度来写深圳,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件事。
郑永年:我回来了以后,国内的地方走的机会也多了,所以我也说,深圳当然取得了太大的成就,我们没有人可以否定它的,但是我觉得要有危机感,没有危机感的城市就很难进步。我在新加坡待那么多年,新加坡是东南亚史上最强、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国家,但是新加坡的总理,从李光耀到李显龙,他的危机感是非常深刻的。
周智琛:没安全感。
郑永年:不仅是没有安全感。一个地方小,李光耀以前说过,中国那么大,3000年以后还是中国,新加坡50年以后能不能、还在不在这个地球上,没有人知道,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。
周智琛:这个危机感如果映射到深圳,我觉得倒真的是非常……
郑永年: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危机感,就像军队必须有假想敌一样。所以深圳同样的,一定要有危机感,向新加坡、首尔这些比你更发达的地方叫板,你才会感觉到危机感。现在有吗?不太多。同样,下一步如果是深圳要上一个新的台阶,跟香港分工合作的话,可以建立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平台——第一个港深的金融中心;第二块科创,结合起来,就是最大的最强的科创中心;第三块科教、教育。
周智琛:对。郑老师,刚才您讲到另外两个支柱,一个是科创,一个是科教,我们也客观地讲,我发现深圳这几年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,或者说可能比其他的城市遭遇更大的冲击,其实就来自于科创。它的产业我觉得一个是,可能就是受全球的这种贸易战或者国际关系的影响,很多被制裁。深圳非常多的这种隐形冠军,或者说全球型的企业,或者说产业链的一些企业,受到很大的波及,包括原创性也受到一些制裁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吧?
郑永年:那当然是危机,政府也在做,但是我是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。当然中国说举国体制,国家承担了一部分的科创任务,但是更多的,从近代以来它的技术发明都是自下而上的发展,所以中国需要这样一套金融体系。如果深圳的科创跟香港的金融体系结合起来,那了不得的,了不得。我觉得龙岗要发展,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你是什么角色,在我们国家是什么角色,或者更高一点,你能不能成为世界上一个耀眼的明星呢?我们要有这个目标去做。
(访谈后)
周智琛:这次跟郑永年教授的对谈,我可以感受到他所推崇的一种交汇的力量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,因为我觉得“交汇”它是一种开放的魄力,也是一种融合的智慧,更是一种包容的格局,所以它也势必带来一种普惠的成果。40年来,深圳其实就是在这种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迅速成长;那么未来,在持续的交汇中,我们同样期待新的深圳故事和龙岗传奇。
(文字整理:程文丽)